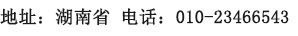牟民每次给93岁的父亲理发,满头白粉似的头屑,轻轻一扑搂,雪花般飘在身上。兑好了水,给父亲洗头。父亲弯不下腰,脖子僵硬,只好母亲端盆,我给抹上洗发精,用手指四处挠着、洗着,父亲会连连喊着,真好,真好!洗过了,他摸着头照例会说,真轻松,不知下次还能不能理发了。话意中流露着伤感。我会大声反驳说,爹,你说啥呢?两个月眨眼就到了。父亲说:我这是实话,都这个岁数了,过了今天,不知有没有明天。母亲在一边说,这老东西,每次剃头,都会这么念叨。我没再说啥,也不必说啥。父亲心中自有人生经验,他虽然不知道倒计时的词语,但对生命看得肯定比我透彻。的确,每一天看起来很短暂,可对父亲来说,那是艰难度日。除了跟身体疾患抗争,还要经受那个不确定时间的折磨。除了吃饭,他便呆在炕上打瞌睡。因为腿疼不能出门,何况耳朵失聪,出门也什么声音听不到,不如不出门。在炕上坐一气,累了,便仰躺在炕头,身下垫了被褥,脸朝上,嘴张着,似睡非睡。如此,身体得不到足够的活动,处处不适,疼痛感随时都有,接连不断地哼哼着。要小便了,他哆嗦着起来,慢慢下炕,拄着拐杖,去院子里方便。虽然身上四处关节疼痛,但父亲走路,脚抬得起来。家里门槛高,母亲经常被磕倒,父亲从没有被绊,战争年代急行军练就的双腿,到晚年还顽强地保留着轻松走路的习惯。白天睡多了,晚上睡不实,小便又频。一会儿让母亲拿尿壶,一会儿咳痰,拿痰盂。父亲耳聋,误认为母亲也听不见,声音大得仿佛吼人。母亲刚刚睡过去了,父亲又叫起来,几乎每天晚上,母亲都没有安稳觉。父亲曾经多次感动地说过,儿女再孝,不如老伴周到。早晨起来,88岁的母亲倒尿壶,倒痰盂,做熟饭,父亲开始起床了。母亲帮着父亲穿衣服、穿袜子,收拾炕。父亲洗了脸,照例在炕上倚着墙壁,说睡不睡的。等到九点,才让母亲弄饭吃。时间在父亲那里,是缓慢而压抑的,每一分钟都浸透着疼痛。相比之下,对于88岁的母亲来说,这时间的流逝却更快一些。母亲70岁后,腰驼了,还有严重的关节炎、腰椎脊椎增生、胃病、胆管结石,除了耳朵比父亲好外,身体不如父亲。晚上,母亲躺不下,躺的时间长了,浑身疼痛。除了伺候父亲,母亲白天不闲着,分分秒秒手里有活儿做。不是洗衣服、抹桌子,就是纳鞋垫,或者到西菜园除草、浇菜。隔五天到三里地外的集市割肉买菜。母亲没时间去思考死亡,即便想到了,也被活儿挤走了。忙碌把多余的无用的思虑忙掉了,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。时间不那么漫长了,它滑滑地溜走了。在父亲那里,那个倒计时没有确定,怕不知什么时候大难来临,提心吊胆。十几年了,每年过了除夕,父亲都会对母亲说,不知能不能吃上下年的饺子了。念叨长了,一家人倒不感觉担忧了,如父亲在念喜歌。我曾经私下想,不管我们儿女愿不愿意,已经活到了九十多岁的父亲,说不行就会不行的,这是客观事实。离家后,在城里,经常电话铃一响,一看是母亲,心里一惊,头上出汗,怕父亲的倒计时结束了。父亲当然也知道,只是不知道这个时辰的确凿信息。仿佛离地头远的人,想想那个倒计时还不急。到了地头的人,迈出去的最后一脚究竟在何时,一把刀已经悬到头顶了,能不想吗?大脑闲着了,死亡一词会缠绕着父亲,这最后的时刻究竟什么时间来呢?如此,这等待是漫长的,当然也是痛苦的。等到两个月后,我再给父亲理发。父亲说,哎哟,又熬过来了。母亲说,咋这么快?说着说着,两个月没了。你说,我都88岁了,数数还要老长时间呢!我会对父亲大声说,爹,你要经常出门活动活动,把时间忘掉。父亲摇摇头,抬抬自己伤残的左胳臂,王顾左右而言他:腿疼。母亲在一边小声说,借着腿疼不走罢了,你爹年轻时就不喜欢出门,不喜欢蹲街头。我说,不愿走,不想活动,他身体、思想更遭罪。遭着吧,人到这个时候,随意。母亲说得挺有意思。父亲喜欢如此,那只有顺着他了。给父亲理着发,他微闭眼睛,静静的,仿佛一个熟睡的婴儿。(壹点号读点)